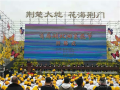《回乡偶书》里的时光针脚
余盛亮
前不久,我和学生一起学习了贺知章的《回乡偶书》。孩子们拖长了调子念:“少小离家——老大回——”那声音清凌凌的,像初融的雪水,淌过我这早已被岁月磨出毛边的耳朵。我让他们停下,问:“你们懂得‘老大回’三个字的分量么?”他们睁着晶亮的眼睛,那里面还盛着满满的、望不到头的未来。他们如何能懂呢?连我自己,在多年前初读此诗时,又何尝懂得!

我的喉头有些发紧。窗外,是这座我寄居了二十余年的城市,楼宇参差,切割着灰白的天。而我的心,却霎时间被那二十八 个汉字拽着,跌跌撞撞,穿过了无数个白昼与黑夜,落回了那条我真正认识的、魂牵梦萦的故乡小河旁。
我的故乡,没有贺知章“乡音无改鬓毛衰”的戏剧性重逢,却有着同样细密而锋利的、时光的针脚。
我想起离老屋不远的那棵歪脖子柚子树。离家的头几年,梦里总见着它,繁茂得像个蓬头的巨人。后来有一年春节归去,我愕然发现,它竟那样矮小,那样瑟缩,枝干在风里显出几分寒伧。不是树变了,而是我的眼睛,被外面广阔的世界与高架桥撑大了。那个曾在它枝桠间攀爬、为摸到一枚蝉蜕而雀跃的孩童,早已被岁月蒸发,只留下一具被公文与尘嚣填满的、疲惫的躯壳,立在树前,相对无言。

这便是“老大回”了。不是荣光,而是一种微凉的确认,确认那段与柚子树、与蝉鸣浑然一体的年月,确确实实是沉入地底,再也打捞不上了。
我又想起更早的、几乎被遗忘的气味。是夏日暴雨前,风卷着泥土的腥气,混着母亲在灶间烧着的、新麦秆的暖香。那气味,是预告,也是庇护。我们一群光脚的孩子,像一群被惊起的麻雀,在雨点砸下前的最后一刻冲进堂屋,浑身汗与尘的味道,立刻被那股更庞大、更原始的家的气味所包裹。而今,我住在恒温恒湿的楼房里,能嗅到的,只有空调送风的微尘气,和偶尔从别家飘来的、千篇一律的饭菜香。那场夏日的暴雨,仿佛再也淋不到我的身上了。
贺知章是幸运的,他终究踏上了故乡的土地,哪怕物是人非,那声“笑问客从何处来”的童音,总归是真实的乡音,是故乡给他的一声带着刺痛的回响。而我们这漂泊的一代呢?我们的故乡,在推土机的轰鸣里,在新修的地图册上,一年年地改变着容貌。它更像一个悬在空中的、由无数记忆碎片粘合的幻影。我们“回”去的,常常只是一个地理坐标;而我们怀念的,却是一整个失落的、由气味、声音与触感构成的世界。

诗教完了,下课铃响起。孩子们像潮水般涌出教室,带着他们那个年纪特有的、对前方世界的无限憧憬。我独自留在讲台旁,窗外暮色渐合,将远方的楼群染成模糊的剪影。
我忽然明白了。我如此执着地反刍着那些关于故乡的、纤毫毕现的记忆——外婆手缝的棉被,那粗粝的触感,傍晚炊烟那直钻鼻孔的呛人而又安心的味道,井水里冰镇过的西瓜那一道清甜的裂痕——我如此害怕它们被时间磨平,或许正是因为,在这些细微的感受里,藏着我自己生命的源头。
我们读诗,教诗,原不是为了注解几个词语,讲清一桩千年前的轶事。而是要在某个毫无预兆的刹那,被那穿越时空的寥寥数语一击而中,恍然看见自己的面容映在那古旧的诗句里,从而懂得所有关于逝去与珍惜的爱。
《回乡偶书》,写的何尝是贺知章一人的还乡?那分明是一根探入所有游子心中的探针,测量着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里,那片故土的深度与温度。
光阴者,百代之过客。我收拾起教案,也收拾起这满腹无端的愁绪。故乡,是回不去了;可那份由这首诗所引发的、尖锐而温柔的怀念,却成了我此刻唯一的行囊。我背着它,继续走在这异乡的暮色里。
作者简介:余盛亮,贵州桐梓人,业余爱好文学,曾在《东方散文》》《遵义日报》《中国新报》等出发表数万余字散文。
相关热词搜索:
上一篇:两县文脉绘新篇
下一篇:他为故乡“装修”未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