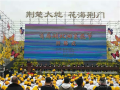午后大雪
赵立文
漫天飞扬的大雪,模糊了双眼,直感到背上的行囊有千钧重,踩在厚厚的积雪中,我无比艰难地行走茫茫雪天中。寒风呼啸,我隐隐听到后背的呼喊,“文伢子,我的儿啊-----”我回头,看见母亲裹挟着雪花,向我狂奔而来。我呆立在雪天中,母亲一把抓起我的行囊,“走,回家!”
许多年了,我常常会从睡梦中惊起,梦境中是鹅毛大雪,它们肆虐、张狂,吞噬母亲弱小的身影-----我眼里的泪水像决了坝的水,倾泻在七尺男儿的脸面上。
那一场午后的大雪,带走了我的父亲。
1989年冬月,我15岁正读初中三年级,那天阴沉沉的,呼呼地刮着北风,一场大雪马上要降临。下午一点多,刚吃完午饭,因是周六没上学,我在邻居家地坪里和小伙伴玩得正嗨。忽然听到隔壁邻居家小四叔在路口急切地大喊:“刘姐,刘姐,快点快点,孩子爸爸出事了。”母亲从井里担着水正准备进屋,一桶水哗的洒落一地。父亲在押煤的途中被------鞭炮在家门口呜咽地炸起尘土,送父亲的车子缓缓地停在我家门前,几个大人抬着父亲进屋,我搀扶着恸哭的母亲,紧随其后,父亲静静地躺在一块木板上,永远地睡着了。
父亲被一场意外的交通事故夺去了年仅39岁的生命。家中的顶梁柱突然倒塌,对一个上有双老、下有俩个正在上学小孩的农村家庭来说,意味着什么。出殡那天,全村的男女老少都出来送别父亲,为父亲丢下的日子而叹息。爷爷不停地捶打胸脯,老泪在他树皮般的脸上纵横,指着老天哭着叫喊:天老爷啊,你怎么不先收走我?!爷爷坐在雪地里用手无力地拍打冰冷的雪,一下,又一下。
漫天的雪砸在漆黑的棺材上,母亲双手紧紧抓住抬棺的绳子死死不放,泪早已哭干,嘶哑的喉咙一遍又一遍地喊着父亲的名字。我神情呆木地抱着父亲的遗像,两腿像灌了铅似的,一步也迈不动,任由飘来的飞雪打在脸上。
办完父亲的丧事,母亲伤心欲绝,身体极度虚弱,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,亲人和邻居都来探望、安慰。我突然长大了,望着母亲惨白的脸,心里有了果断的决定,悄悄地对妹妹说,你坚持读书,我去南方……
我悄然地打起行囊,在父亲上山后的第七天,一头扎进了雪天中。当母亲追来,抓夺我的行囊时,我执拗地要夺回,母亲一声吼叫,“文伢子,除非我死了,你再去打工!”她洒了一把泪水,在漫天雪花中,站成了棵松柏。
受村里的关照,母亲去了村办砖厂食堂做事,村办砖厂约有80个劳力吃饭,那时建中村办砖厂红砖质量好,销路不成问题,岳阳县三田一洞的村民建房户及周边企业纷纷来拉砖,晚上经常打夜工做砖,食堂里加班加点也是常事。
作为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,要独自抚养2个正在上学的小孩,还有公公婆婆需要赡养,实在不易。也有好心的邻居说:“刘姐,你看儿子也初中毕业了,不如送他去学一门手艺,一个人太难了。”邻居说这话时,我没在场,是听妹妹说的。后来,只上了小学三年级的母亲对我说:“文伢子,我冒读什么书,你再不要有辍学去打工的想法,就是砸锅卖铁也要送你上高中啊!”当时我的确再次有去南方深圳打工的想法,因为妹妹也在上初中,家里经济条件实在不允许两个孩子上学,几次话到嘴边,看到母亲坚毅的神情,我只好答应去读书。
“文伢子,你再也不要三心二意,天大的事,我来想办法。”母亲当时每月工资只有90元,爷爷奶奶体弱多病需照料,自己省吃俭用,全力供我兄妹俩读书。
1990年那个冬天,郭镇镇上至村办砖厂未通公交车,食堂每隔两天要去市里买菜,母亲和食堂的李师傅都要走5公里的路到镇上,然后搭乘7路车到市里面买菜。窗外飘着小雪,时不时还夹着雪团落下,看样子一时半会还停不下来。
“刘姐,我们今天不去市里面了吧?李师傅在问。“不行呢,食堂没菜了。”母亲在里屋回答。母亲和李师傅买菜回来到了镇上,已近中午12点,外面的雪越下越大,仿佛无数扯碎了的棉花球,从天上翻滚而下。李师傅说:“刘姐,你如果肚子饿,就在镇上吃碗面吧,下雪天空着手在路上走也是滑溜滑溜,更何况担着160余斤重的菜,一个小时的路程,就连我们男人也吃不消啊。”母亲哪舍得吃碗面的钱?咬咬牙,挑着菜,一头扎进雪地里。
临近中午一点,母亲买菜还未回,我看着桌子上的钟表,窗外北风呼啦呼啦、雪花铺天盖地,不能再等了。我抓起棉帽戴在妹妹头上,和她各拿了一个蛇皮袋子,顶着风雪去找母亲。兄妹俩艰难步行进着,前面隐隐约约有个挑担的身影,啊,是母亲,是成了“雪人”的母亲。她见是我和妹妹,缓缓放下担子,大声呵斥:这么大的雪,你们出来干啥?风雪拍打在兄妹俩的脸上,也拍打母亲柔弱的身躯上,我们不由分说,便从箩筐里拿出菜往准备好的袋子里装。我和妹妹背着菜,母亲挑起担子,娘仨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走着,原来路是那么地漫长啊,我第一次体会了母亲所走过的路长而不平,这何尝不是血脉相连的路?
回到食堂,母亲刚放下担子,便大声吩咐:文伢子,你和妹妹赶快去换衣服,不要感冒了。我回头一望,母亲的衣服已湿透,脸上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下,一双胶鞋里面全是雪水,拧着脱下来的袜子,水滴滴下落,我鼻子一酸,泪水哗哗流淌。
临返校的晚上,母亲又忙碌起来,张罗着给我做菜,说是带学校,怕学校里面伙食不好。因第二天还要早起返校,我早早睡下,不知睡了好久,朦朦胧胧中,家里的灯亮着,母亲还在灯下缝补衣服,我用被子擦了擦眼睛,心头不知是啥滋味。
第二天一大早,我匆匆地背上书包,正准备上学去。“文伢子,你稍等哈。”母亲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手绢,像是包着什么东西从里屋快步走来,她慢慢地打开手绢,包了好几层,里面是几张皱皱巴巴的拾元钞票和一些零钞。母亲用食指蘸了下嘴唇,数了一遍,小心翼翼地挑了3张拾元的,塞在我的裤兜里。母亲望了望,用那双结满老茧的手,摸着我的头,低沉地说:文伢子,读书要认真啊,你可要为家里争口气!短短的两句话,重若千钧,泪水在我眼眶里打转转,好久好久滴不下来。要知道,母亲一月才几十元钱,我们两兄妹读书,家里日常生活开支,还有年迈体弱多病的爷爷奶奶每天打针吃药,不能间断。
学校放暑假了,我望着母亲忙碌的身影,心里寻思着:想打份短工,为家里补贴下家用。我瞒着母亲,找到砖厂制坯组的李组长,说了来意。李组长用怀疑的眼神瞄了一下我瘦瘦的个子,“文伢子,这可是体力活,你吃得消不。”李组长实在拗不过我,只好答应我明天去试下工。
第二天,我早早来到砖厂制坯组机房,李组长安排我拖板车。其实,拖板车的活就是用板车接下制坯机房切下的砖坯拉到砖厂大操坪,再由码转的师傅码起来凉晒。我定了下神、猫着腰,双手拽紧装上砖坯板车的把手,还挺沉,生平第一次拖板车,那板车老是不听使唤,拐弯时不知道是不是用力没用好,板车差点翻了。李组长快步上前帮我把了下板车,“文伢子,要不你还是算了-----”临近上午11时,室外气温高达40度,刺眼的强光刺得眼睛发痛,汗水顺着脸颊一滴滴往下落,我咬咬牙,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一把汗,拉起板车继续前行。晚上收工回家,我腰直不起来,发现白天干活穿的衣服背后有一层流汗过后的白色盐渍,双手抓板车的地方起了泡。母亲拿起我的手,心痛地说:文伢子,你明天不要去了。“您放心,我能坚持住。”
一晃一个月过去,“文伢子,你来下,把做事的工钱结给你。”我接过李组长给的工钱,一路小跑,心里如同喝了蜜一样甜,要知道,这是我第一次凭自己劳力挣的工资。当我把从李组长那里结的5张夹杂着汗渍味的一百元红票子交到母亲时,她愣了一下,盯着我看了半晌,眼里扑闪着光亮,拉着我晒得黝黑发亮的手臂,摸着我的头,“我文伢子懂事,可以赚钱了。”
1992年,我高中毕业,在大舅和母亲的支持下,我响应祖国的号召报名应征入伍。临出发的晚上,母亲一遍又一遍检查我的行李,生怕拉下该带的物品。因母亲前段干活腿受过伤,我不让她送行。第二天一早,我怕惊醒母亲,我悄悄背上行囊去火车站,“文伢子,你等一下我。”我转身循着声音望去,母亲拖着受伤的腿,一瘸一跛地走过来。“到了部队,记得给我写信,不要想家,安心工作。”我眼里含着泪花,转身登上绿皮火车,随着汽笛响起,火车缓缓驶出车站,母亲仍在站台上不停地挥手,车窗外母亲瘦小的身影却分外高大。
火车把我拉到了遥远的西北边陲,来到了向往已久、火热的军营,我光荣地成为了新疆武警部队的一名战士。12月份的新疆伊犁,仍是白雪皑皑、天寒地冻,远处的天山终年为冰雪覆盖,远远望去,那闪耀着银辉的雪峰,是那样雄伟壮观、庄严而神秘。我忽然想起故乡午后那场雪,这场刻骨铭心的雪在西北边陲也有异曲同工之妙,母亲就是守护在我心头上的神。
新兵训练临结束,团部组织全副武装5公里考核。排长带着我们来到考核场地。这天下起了蒙蒙细雨,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哨响,我们如射箭般冲了出去。雨大了起来,在眼前织了一张浓密的网,5公里考核还有最后800米,我攥紧胸前的冲锋枪,和战友们向终点冲刺。雨天路滑,在拐弯处,我崴了脚,疼痛难忍,步伐速度明显降下,肩膀上背的装备仿佛千斤重,雨水和汗水顺着脸颊流下,每前进一步都分外艰难。排长跑来,“小赵,你受伤了,实在不行,就不要跑了。”正在犹豫中,我脑海蓦地闪现了母亲在风雪中担菜前行的画面,耳旁仿佛听到母亲的声音,“文伢子,坚持就是胜利!”在排长和战友们的鼓励下,我坚持到了终点。
儿行千里母担忧,识字不多的母亲来到砖厂会计办公室,“小王啊,有空么?”“刘姐,有什么事?”“麻烦你帮忙给文伢子写封信啰,叫他要听首长的话,安心工作,刻苦训练。”在母亲的鼓励下,我在部队入伍第二年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,多次荣获“优秀士兵”。
“刘姐,文伢子来信了”,当邮递员把“优秀士兵”的奖章送到母亲的手中时,她双手接过奖章,用手帕仔细擦了又擦,喃喃自语:我文伢子长大了,有出息了!
2007年,我脱下军装,回到地方工作,而母亲已白发满头。她就像神一样,在我的睡梦中出现。那个大雪飘飞的午后,扁担压迫着她的双肩,而她的坚定一直给了我方向和力量。
又是一个周末,艳阳天,我和妻子、女儿来到赵家里,推门不见母亲,顺着屋前地坪往田野望去。不远处,一个熟悉瘦小的身影还在菜园里忙碌劳作。此刻,屋前树上的芙蓉花在阳光下迎风绽放,开得正艳。
作者简介:赵立文,岳阳市作协会员,12年军旅生涯。毛泽东文学院岳阳作协专修班学员,作品散见《湖南道路运输》 《一线诗刊》 《珠海特区报》 《绥化日报》 《岳阳日报》 《岳阳晚报》等。
相关热词搜索:
上一篇:租一段好时光
下一篇:省级非遗“活”起来 苗年民俗润童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