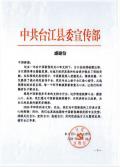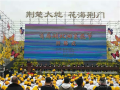江山泉记(一)
余盛亮
贵州省桐梓县水坝塘镇木江山村的晨光,总先落在江山泉的井台上。这眼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井,依着村宅的墙根而生,青石板井栏被世代村民的手掌磨得温润,像一块浸了岁月的玉。井台边的石缝里钻出几丛艾草,风过处,气息混着井水的清冽,漫过白墙黑瓦的村落。

村里人说,江山泉最神的,是土地革命那阵子。那年大旱,方圆几十里的水源都见了底,唯独这口井,泉水咕嘟咕嘟往外冒,清得能看见井底的鹅卵石。驻在村里的解放军战士就靠这口井解渴,几十号人每日打水、挑水,井台边的脚印叠着脚印,水桶撞在井壁上的声响,成了那段艰苦岁月里最踏实的节拍。
木江山村的晨雾还没散时,江山泉的井台已先醒了。青石板被三百年来年的脚掌磨得发亮,像一块浸在水里的墨玉,映着周围的桃树与柏树。井水从石缝里汩汩冒出来,带着山根深处的清冽,把晨光泡得软软的,连落在水面的桃叶,都像是在轻轻摇晃。
守井的娄爷爷说,这泉眼是“诚实”的。旱季不偷懒,雨季不贪多,就那么稳稳当当地涌着,像村里的老辈人,话不多,却把力气都用在了实在处。土地革命时期,四邻八乡的井都干得裂了缝,唯独这里的水依旧旺,驻在村里的解放军战士喝着这水,帮着村民挑水浇苗,临走时摸着井栏说:“这井里有股子实在劲儿。”后来听说,那批喝泉水的战士里,出了好几位扛得起事的干部——就像这泉水,不声张,却养出了能担事的骨头。
从井边走出去原村民娄义珍,身上就带着这股实在劲儿。
老人们常说,她小时候总在井边转,帮着家里挑水,桶绳勒得肩膀红,也没喊过一声累;娄义珍忙完后,会蹲在井边帮娘洗菜,泉水溅在布鞋上,笑得眉眼弯弯。如今他们在远方做事,每次打电话回村,头一句总问“井里的水还旺不旺”,仿佛那口井是系着心的绳。
而今,这口老井正被村里人小心地护着。娄爷爷站在井台边,手里拄着拐杖,嗓门却亮得很:“这井养了咱三百年,不能让它坏了!”一声号召,村民们全来了——年轻的搬石块,年长的和水泥,妇女们端着茶水往工地送,孩子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,用小铲子把井边的碎石堆到一起。
“得把井栏重新砌牢实,再修个挡水沿,免得雨水灌进去。”娄爷爷用拐杖敲着旧井栏,“当年部队喝这水,现在咱喝这水,将来娃们还要喝,得让它干干净净的。”泥瓦匠师傅蹲在井边,仔细量着尺寸,灰浆抹得匀匀实实,像是在给老井缝件新衣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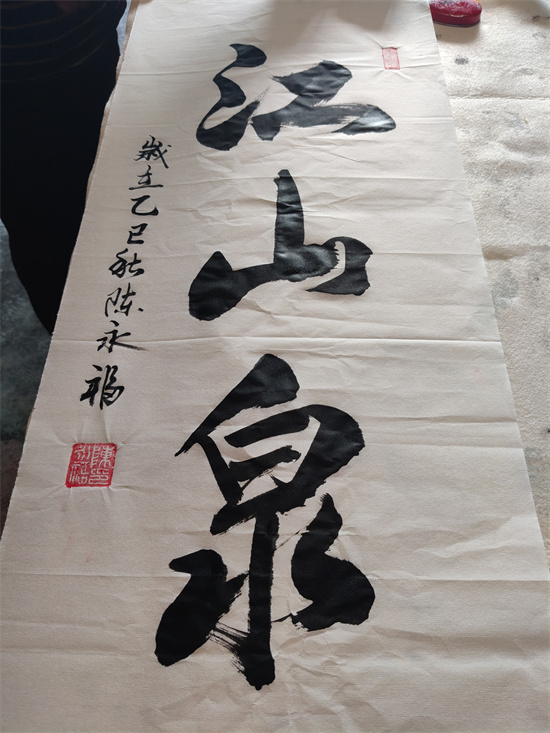
井台上的艾草被挪到了旁边,露出底下青石板的纹路,那是三百年间无数双脚踩出的痕迹。有村民用软布蘸着井水,一点点擦去井栏上的泥垢,擦着擦着,忽然说:“你看这石头上的印子,多像娄家娃小时候挑水磨的。”大家都笑了,笑声落在水面上,漾起一圈圈涟漪。
维修的日子里,井台比往常更热闹。白天,叮当的凿石声混着说笑声;傍晚,收工的人们坐在井边的石凳上,听娄爷爷讲过去的事——讲大旱时泉水如何救了全村、讲战士们挑水时如何小心不踩坏田埂、讲娄义珍和土改战士当年如何在井边立志要好好革命,将来为国家和家乡做事。
泉水依旧静静涌着,映着维修的人们,也映着天边的晚霞。它见过革命年代的烽火,见过走出去的游子的背影,如今又见到村民们守护它的模样。娄爷爷说:“这井啊,就像咱木江山村的根,根扎得深,树才能长得高。咱护着它,就是护着这份念想,护着走出去的娃们心里的家。”八十年代初的木江山村,路是“晴天一身土,雨天两脚泥”,夜里黑得像泼了墨,田地里的庄稼全看老天爷脸色。那时娄义珍刚到省里工作,回村探亲时,踩着没脚踝的泥路走到井台边,蹲下身掬了把泉水,水凉丝丝的,却让她眼眶发热。“路得通,灯得亮,地得有水浇。”她跟村干部说这话时,手指在井沿的凹痕上摩挲着,“咱不能让泉水白养咱。”
没过多久,省财政厅的拨款就到了。推土机轰隆隆开进山坳,把蜿蜒的土路拓成了能走汽车的石子路;路灯杆一根根竖在了村口到井台的路上,傍晚一亮,像串起了一串星星;灌溉渠顺着山势绕,把江山水引到几百亩田地里,禾苗喝足了水,绿得能掐出汁来。通车那天,村里的老人们摸着光滑的灯柱,看着渠里流淌的泉水,眼眶都红了:“这水,终于能跟着路跑了。”娄爷爷记得,娄义珍那天就站在井边,看着村民们在新修的路上来回走,手里的搪瓷缸盛着井水,喝得比蜜还甜。
娄义珍不常回村,却总让人捎话问井里的水旺不旺。有年春天,她托人带回来一批新的桃树苗,让栽在井台周围,说“让泉水边多点生气”。如今桃树成林,春天开得满树粉红,花瓣落在井里,像给泉水戴了串花项链。
村里在外读书的年轻人回来,总爱趴在井栏上喝水,说“城里的矿泉水,没这股子清甜”。娄爷爷就会跟他们讲娄义珍的事,讲她修的路、安的灯、引的渠,末了总说:“都是泉水教的。泉水从不显摆,却把好东西都给了咱;走出去的人,也该这样。”
如今的江山泉,依旧每日涌着清水。村里的自来水早已通到家家户户,可老人们还是习惯来井边打水,说“这水烧开了没水垢”。孩子们放学后,会趴在井栏上看水里的云影,听老人讲当年部队打水的故事,讲那些从井边走出的人如何在远方发光发热。
井台上的青苔枯了又生,井里的泉水涨了又落,像在默默诉说:真正的力量从不是喧嚣的,就像这眼泉,三百年如一日,用清冽滋养着一方水土,也滋养出一代代踏实做事的人。江山泉的水,还在流;从这里走出去的人,初心也从未变过。井台上的柏树枝繁叶茂,影子投在水里,随波轻轻晃。娄爷爷坐在石凳上,看着泉水里的云影,忽然懂了:江山泉哪里只是口井呢?它是木江山村的魂,是走出去的人心里的秤。它教给人的,从来不是轰轰烈烈,而是默默付出——就像娄义珍,不声张自己做了多少事,只把家乡的路铺得更宽,把日子照得更亮,让泉水滋养过的土地,长出更多希望。
夕阳把井水染成金红色时,娄爷爷提着水桶往家走,桶里的泉水晃悠悠的,像装了一汪星星。他知道,这泉水会一直流下去,就像那些从木江山村走出去的人,无论走多远,心里总有那么一眼泉,装着对家乡的惦念,踏踏实实,从未变过。(口述:娄练 整理:余盛亮)
相关热词搜索:
上一篇:微型小说|娄义华: 偏不坐免费车
下一篇:《我与国庆》(外二首)